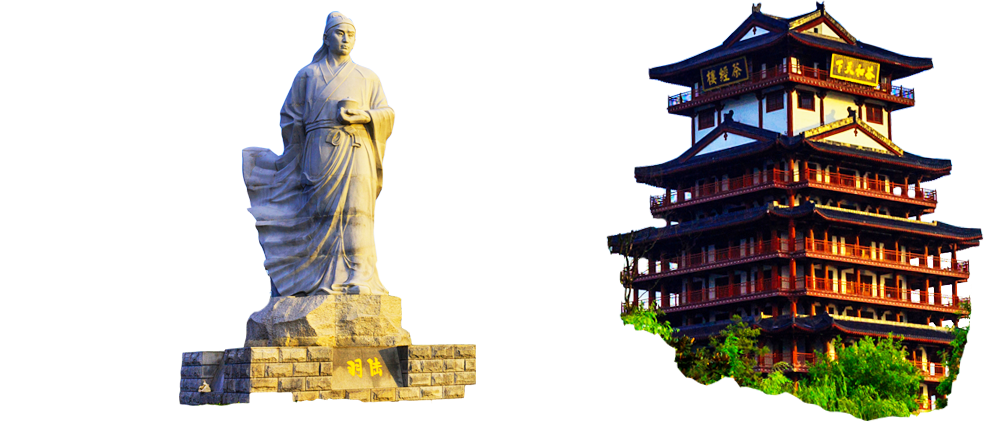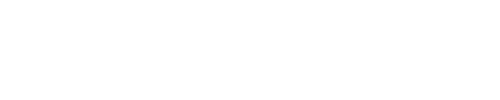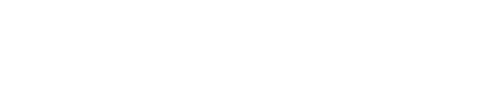五年前,我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谈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是如何超越西方模式的。
西式民主是保底的“下下策”
我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是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在中国,领导人要么担任过省级领导职务,要么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治理中国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加起来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和日本过去一些年里的平庸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选举”的模式完全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不合适的领导人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尽可能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
西方政治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
五年过去了,我的这些话依然有效,因为它准确概述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令人感叹万千的是:五年时间飞逝而过,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产生的一流领导人及其团队推动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产生的平庸领导人导致西方世界更快地衰落。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领导人,原因就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此外,西方国家普遍陷入财政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庸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
中国较好地结合了“选拔”和“选举”
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1978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确保国家全面现代化目标的如期实现,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强调需要通过选贤任能,从组织上保证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较好地结合起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和梯队。这套制度建设意味着,大部分领导干部的晋升都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经过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最后才能担任关键职务。虽然这种制度设计还有不足之处,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足以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竞争。过去数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和西方的持续衰落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举措》)、“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贞观政要》)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格格不入。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这种集古今优势和中外长处为一体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大制度保证。
中国可为解决“柏拉图之问”提供经验与智慧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选举政治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患了病,你是到广场上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百倍于治疗一种疾病,你该找谁呢?柏拉图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很多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良好宪政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着称的德国人却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同样,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西方世界各种“黑天鹅”现象频发的状况,估计他也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自由派曾创造出一种“制度万能论”的话语:只要制度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选个傻瓜治国也没有关系。但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随着中国和中国模式的迅速崛起,这种“制度万能论”不攻自破,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也不会接受了。更何况,不同的制度各有优势,西式民主绝非最好的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有其优越性。
中国人经过百折不挠的探索终于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今天可以为许多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